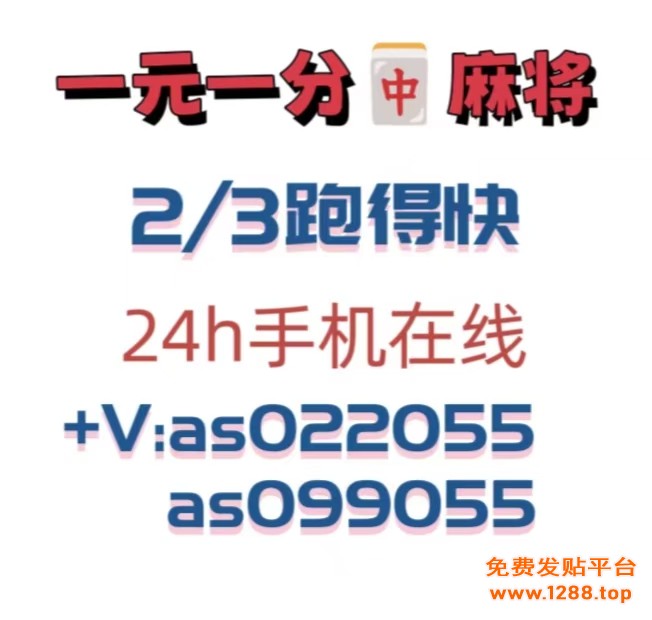
暖被窝这一纯体力劳动耗掉的是热量,沾染的却是一种母性特征明显的温情
我虽然不是膀大臂圆,但好歹也是个男人,最受不了的是梅兰芳、兰花指和太监,不料孵了几次被窝,我身上的暴戾之气渐去,心境竟平和如佛,人在大千世界,心里却默念着“一时佛在舍卫国……”这样一心向佛地把被窝暖得接近了体温——37度,这是世上多么富有人情味的一个温度,它在感觉层面上带给人的美学效果,基本上相当于黄金分割点带给视觉的绝佳匹配
那块洋芋地距家一两里路吧!那块麦田可能还要远一点
一天,侍女们都去了花圃,密斯到达高层的谁人窗户下,把餐桌、茶几、椅子一个挨一个地摞成一个塔,爬上了小窗沿
从窗口往外望去,只能见到天际、乌云和太阳,看得见地,但能听到大地上传来的声响和话语
那时候,我发现了身体的供给和供出,要单单养活一个躯体,满足它的成长过程,需要付出所有,需要那么一种身体和灵魂朝向的倾斜姿态,并通过精神的和肉体的劳动,实现心中的目标
这些行为,一开始就在动荡不宁当中,在日月潜行,在风月雷电,在人和庞大的世界撕扯中,呈现出巨大的不平衡
而这些必然的倾斜姿态,其实质是在做着企图还原这个世界平衡的种种努力
面对生的忧患,他俩宁愿遁入首阳山采集野菜,咀嚼大自然的英华,充当历史王道中的英雄角色,也不愿随波逐流
百年以后的孔子在《论语?述而》中讲到,“德之不修,学之不讲,闻义不能徙,不善不能改”
如此大忧大患和伯夷叔齐的“神农虞夏忽焉没兮,吾适安归矣吁嗟徂兮”的忧虑和不归相比,简直如出一辙
难怪同为儒家学范的他们,要被后世立为历史王道里的道德标向
在哲学意义上讲,“无用性”标志着肉身与精神的彻底断裂
信念、理想抑或希望一旦陷入“无用”,那么,精神的生命又将何复以求呢?虚无的深渊,绝望的深渊是真正的归宿
《圣经》中有亚伯拉罕的绝望,约伯的绝望,耶酥的绝望,而伯夷叔齐的绝望就是宁可“饿且死”,亦不归
信念欠缺乃至于对人世的欠缺的认识,把伯夷叔齐逼上绝路
登上首阳山,也就意味着对自己精神的反叛和放逐
屈原有《天问》,高士有《采薇》
一个投江,一个饿死
尽管选择的方式不同,但求道无门时的解脱却极其相似
体面地与那个格格不入的世界告别,其实也是希冀在冥冥的逍遥之中得到拯救,一种内心的拯救,和信念的拯救
“他愈嚼,就愈皱眉,直着脖子咽了几咽,倒哇地一